


本组图片:拉布列德城堡
当年严复翻译孟德斯鸠的那部大作时,曾将书名译为《法意》。这本书在中国最早的译名是《万法精神》,直到有了后来的白话译本,才正式出现了那个众所周知的大名:《论法的精神》。书中的“三权分立”学说和书名一样,成为后世大多数人眼中孟德斯鸠的标签。不过,孟德斯鸠自己当年说过一句含义暧昧的话:“自从和平恢复以来,我的酒在英国为我赚的钱一直比我的书(《论法的精神》)为我赚的钱多……我不知道是我的酒增加了书的名气,还是书增加了酒的名气。”
孟德斯鸠所说的酒是葡萄酒。在他那个褒贬不一的法庭庭长身份之外,孟德斯鸠确实还扮演着葡萄酒商的角色,英国则是当时最重要的葡萄酒销售市场。按照近年流行的《达·芬奇密码》式考证逻辑,有人曾不完全开玩笑地提出:《论法的精神》原文名为“l’ Esprit de Lois”,其中“精神”(esprit)一词兼具主要以蒸馏酒为代表的“烈酒”的含意,译为英语的“spirit”后也是如此,因此孟德斯鸠在大书特书“法意”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推广“酒的精神”或称“酒精”,整部《论法的精神》进而可以理解为孟德斯鸠为葡萄酒所做的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型广告文案。《论法的精神》序言里有一句:“如果人们愿意寻找作者的意图,只能在著作的总体意图中寻找和发现它。”按照上述演绎,句中的“意图”(dessein)也被还原为它原有的“目的”、“规划”、“设计”、“企图”甚至“阴谋”意味,而这个神秘的“dessein”指的不是别的,正是孟德斯鸠在表面的政论文字之下经营的葡萄酒推广计划。
当然,对于正统学者来说,上述说法只是些不值一提的坊间怪谈,但对于葡萄酒历史文化研究者来说,孟德斯鸠并非躺着中枪,算不得冤枉。白纸黑字的事实是,如今葡萄酒界最时髦的“风土”(goût de terroir)概念最早系统出现正是在《论法的精神》中,而且孟德斯鸠去世后的一份资产清单清晰地显示,他的领地确实在生产葡萄酒。同样出身波尔多的法国历史学家拉古图(Jean Lacouture)在他撰写的孟德斯鸠传记中说:“他真的非常喜欢葡萄酒,并真的为之乐此不疲地工作。”
现代葡萄酒界一般将“风土”定义为:葡萄园中土壤、方位、气候、园内小气候、排水坡度及其他一切相关因素的组合;即使相邻只有1米距离,每处葡萄园的风土条件也可能完全不同,出产的葡萄的品质因此出现高下之分,进而影响到最终成酒的质量。在《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人受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准则、先例、习俗、风尚等多种因素的支配,其结果是由此形成因地而异的普遍精神。”孟德斯鸠没有使用“terroir”一词,但他对气候(climat)的强调已经颇引人注目。正如英国语言哲学家夏克尔顿(Robert Shaekleton)在《孟德斯鸠评传》中所言,“climat”,也即英语中的“climate”一词,“原意是指地球上相隔一定距离的两条纬线之间的空间,后来词义扩展、单指地理位置……孟德斯鸠是第一个用‘climat’表示‘气候’的学者”。用词上的差异并不能抹杀孟德斯鸠对风土学说的贡献,何况“climat”如今至少在法国勃艮第已经成为比“terroir”更加“儒雅”的说法。
有学者断言,孟德斯鸠实际上是“地理环境决定论”(Determinism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s)的先驱之一。抛开学术界对于地理决定论的争论,纯粹从更“朴实”的葡萄酒酒业眼光来看,法国从中世纪修道院年代世代沿袭下来的葡萄种植经验对孟德斯鸠的思想很可能产生了重要影响。孟德斯鸠本人出生地乃至《论法的精神》诞生地的“风土”也很明显地显示:象牙楼阁般绕开这些经验是不可能的。
没错,孟德斯鸠诞生在一个人人都不得不谈论葡萄酒的地方:法国波尔多(Bordeaux)。他的出生地拉布列德城堡(Chateau de la Brède)至今仍完好地矗立于波尔多南郊,自1951年起被法国列为国家历史遗产。历史上,拉布列德城堡是孟德斯鸠家族名下的产业之一。谈及孟德斯鸠的城堡,首先必须厘清一些事实。最基本的一点是:孟德斯鸠严格意义上并不叫孟德斯鸠,他的准确名字是颇有些繁琐的“夏尔-路易·德·瑟贡达,拉布列德及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Louisde Secondat,Baronde La Brèdeet de Montesquieu)。

自1951年被法国列为国家历史遗产后,拉布列德城堡内经常定期举办文化沙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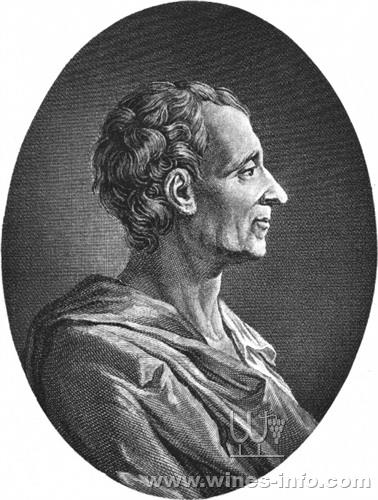
孟德斯鸠
在拉布列德东北方向、加龙河(Garonne)河畔有一个市镇,名叫“孟德斯鸠(Montesquieu)”。孟德斯鸠镇占地2554公顷,是法国最大的市镇之一。从1162年的一份文献上可以看出,孟德斯鸠镇古名为“Monteschivum”。如果将镇名拆分成“Mont-Esquieu”便很容易理解它的原意,因为后半部分在古奥克语(Occitan)中为“esquiu”,意即“蛮荒”、“陡峭”,前半部为“山岭”,恰如其分地描述了孟德斯鸠镇所处的地理位置。孟德斯鸠形成市镇始于1349年,这里原本是现今法国与西班牙临界处的纳瓦尔王国(Navarre)的领地,1589年随着纳瓦尔国王亨利三世继承法兰西王位、成为亨利四世并入法兰西,而亨利四世正是法国波旁王朝(Bourbon)的第一个国王。
哲学家孟德斯鸠姓名中第一个“德”后面连接的才是他真正的“祖籍”与姓氏。瑟贡达家族发源自法国中部、卢瓦尔河(Loire)流域的贝利(Berry),15世纪后南迁至现法国多尔多涅省(Dordogne)的阿让(Agenais)地区,效忠领主阿尔布雷(Albret)家族。1564年10月,也即法国南部以纳瓦拉王国为代表的新教胡格诺派与法国北部天主教派之间的宗教战争刚起战火之际,纳瓦尔国王亨利三世的母亲、有“新教胡格诺派精神领袖”之称的让讷·德·阿尔布雷(Jeanned’Albret)王后因为“优秀而忠诚的服务”将孟德斯鸠地区的领地辖权赐给让·德·瑟贡达(JeandeSecondat),瑟贡达家族由此成为孟德斯鸠地区的领主。1606年2月,已登上法国王位的亨利四世将孟德斯鸠地区升格为男爵领地,并赐予让的儿子雅各布(Jacob)、也即未来的哲学家孟德斯鸠的曾祖父。
在孟德斯鸠镇确实有一座孟德斯鸠城堡(ChateaudeMontesquieu)。它建造于14世纪,位于加龙河河谷边险峻的峰顶,居高临下,俯瞰全镇,自建成以来见证了包括英格兰占领、海盗入侵、宗教战争在内的数次战乱。这座城堡或许也记载了孟德斯鸠家族早年的荣光以及他们与波旁王族的“草莽之交”,只可惜在哲学家孟德斯鸠生活的时期就已经处于半荒废状态,虽然至今尚存,但已几成废墟,仅存三座大门、一个警卫室、一口深井。如今它甚至已经不是孟德斯鸠家族的产业,仅凭顾名思义去怀古的人未免会枉自买椟还珠。
真正对于哲学家孟德斯鸠来说意义非凡的是拉布列德城堡。除童年时光外,孟德斯鸠成人后也长期居住于此。正是在拉布列德城堡,孟德斯鸠完成了《论法的精神》部分章节的写作。拉布列德村位于波尔多以南18公里处,尽管在占地面积上无法与孟德斯鸠镇相比,但400多年来的人口变迁或许能暗示出这两处村镇的某些不同:根据法国官方统计,在1821年人口数量巅峰期,孟德斯鸠镇拥有居民1550人,随后逐年下降,2010年降至780人;拉布列德村在1793年就拥有1324居民,时至2010年已增加至3825人。
拉布列德城堡建筑在一片约150公顷的树林里,林中有美国橡树、鹅耳枥、洋槐、板栗,野鹿、野鸡等动物时常可见。城堡始建于1306年,带有与传统堡垒不同的多边形围墙,宽阔的护城河中生活着大批鲤鱼,曾经有三座吊桥连接外界,如今已经改成一道固定的木桥。拉布列德城堡曾经分别隶属拉兰德家族(La Lande)、历斯勒家族(l’ Isle)以及佩斯内尔家族(Pesnel)所有。1686年,与玛丽-弗兰索瓦·德·佩斯内尔(Marie-FranÇoise de Pesnel)的联姻使城堡成为瑟贡达家族的产业,而当时的新郎雅克·德·瑟贡达(Jacques de Secondat)正是未来的哲学家孟德斯鸠的父亲。哲学家孟德斯鸠自出生便注定拥有“拉布列德男爵”的封号,“孟德斯鸠男爵”的封号却是在16年后偶然得自伯父的馈赠。

“英国自然式园林先驱”培根认为:“种植花园是人类乐趣中最为纯洁的事”

培根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鸠诞生在拉布列德城堡,直到3岁一直居住在拉布列德乡间。拉布列德城堡外有一片14世纪的农舍。孟德斯鸠生活在城堡中时,这里是一所“拥有三座彼此连接的房屋的颇具规模的小动物园”,里面饲养着各种牲畜和家禽。成人后孟德斯鸠曾这样描述当地人的生活:“一日三餐是燕麦面包、玉米糊,偶尔也喝黑麦糊……他们信神信鬼,尤其信巫师……他们哄孩子们时喜欢讲神话、讲鬼怪故事,他们甚至还说得出魔鬼们最喜欢在哪些地方与本教区的巫汉和巫婆聚会……我记得,小时候若是独自夜里到了那里,就吓得浑身发抖,特别是那块不长草的地方,因为魔鬼们最喜欢在那时跳舞。”这位“启蒙与理性之父”的童年就这样在神鬼陪伴下度过。1700年,11岁的孟德斯鸠按照家中的安排前往巴黎附近的奥拉托利会学校(Oratorian School)。从小在庄园里长大的孟德斯鸠和拉布列德村村民一样,操一口加斯科尼方言,而且终生乡音未改。后来孟德斯鸠在《波斯人信札》(Lettres Persanes)中写到,他的南方口音曾遭巴黎的同学嘲笑,但“想改也难”。
如今拉布列德城堡第一道大门门楣上的铭文是“O rus quando te aspiciam”,原句出自贺拉斯,意为:“哦,乡间,我什么时候能够再见到你。”镌刻这一铭文是孟德斯鸠的设计,不过他最初对拉布列德乡间的思念可并不如此单纯。1705年,孟德斯鸠重返波尔多。孟德斯鸠家族早在16世纪就获得了波尔多高等法院庭长的世袭职位,孟德斯鸠的伯父让·巴普蒂斯特·德·孟德斯鸠(Jean Baptiste de Montesquieu)作为家中的长子继承了庭长一职,当让·巴普蒂斯特的独子不幸夭折后,他便决定将自己一切职务、财产和爵位的继承权遗赠给侄儿,作为交换条件,孟德斯鸠必须攻读法律。
波尔多的4年学习之后是巴黎近5年的律师和法官助手实习工作。1716年,伯父去世,年仅27岁的孟德斯鸠成为波尔多高等法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庭长。孟德斯鸠的伯父曾被称誉为“当时最杰出的法官之一”,应该是为“工作便利”,当年的夏尔-路易·德·瑟贡达此后开始广泛使用“孟德斯鸠男爵”的名号。
尽管家境殷实、出身名门,1725年,孟德斯鸠在名为《审判与执法应以公平为准绳》的演说中仍感慨:“法官们终日面对各种各样的诡计和突然袭击,于是真理和谬误使他们同样不敢轻易置信……法官的难处与其说在防备辩护人作伪,毋宁说在于对付那些他为之尽心竭力的人的诡计。”1726年,孟德斯鸠出售了家族世袭的庭长职位,仿佛饯行了自己在5年前的《波斯人信札》中所说的:“当我认识到什么是恶的时候,我远离它并揭露它。”1728年,孟德斯鸠经过德国、奥地利前往意大利,不久又折返北上,抵达英国。1731年,孟德斯鸠返回波尔多,定居拉布列德城堡,在这里相继写出了《罗马盛衰原因论》(Conside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ecadence)和《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的祖辈经历了体现法国从单一天主教到接纳新教转变的宗教战争,曾在天主教学校学习,后来迎娶一位信奉新教的新娘的孟德斯鸠似乎也继承了家中的自由传统,何况他原本就伴随英国“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而生,又目睹了法国由路易十四到路易十五王位更换的敏感时期。后世学者普遍认为,在英国的游历对孟德斯鸠的政治哲学影响颇大,而对于拉布列德城堡来说,孟德斯鸠从英国带回的最直接影响体现在它的花园上。
孟德斯鸠将拉布列德城堡原有的风格称为“哥特式”。城堡虽然在文艺复兴时期顺应潮流进行过一些改造,但显然还不符合孟德斯鸠的品味。英国之行使孟德斯鸠接触到英式花园并决定仿效,如今环绕城堡的花园便为孟德斯鸠亲自设计:广阔的草坪伴随着缤纷的观赏植物,人们可以从三条通道以不同的角度欣赏城堡外以白色蔷薇覆盖的不同立面,花园中的日晷以及如茵的草坪与城堡原有的冰冷风格形成对比。在城堡第二层的房间里,提供了很多观景点供人们欣赏园中景色。在写给朋友古阿斯科(Abate Ottaviano Guasco)的一封信中,孟德斯鸠曾说:“你不想再来参观一下拉布列德城堡吗?自从你上次拜访之后,我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如今它是我所知道的最美妙的乡间居所。”

赫许城堡的酒窖

巴克龙酒庄的葡萄园
欧洲的造园艺术有过三个最重要的时期:从16世纪中叶往后的100年,是意大利领导潮流;从17世纪中叶往后的100年,是法国领导潮流;从18世纪中叶起,领导潮流的就是英国。彼得·柯林斯(PeterCollins)1965年的经典著作《现代建筑设计思想的演变》(Changing Ideals In Modern Architecture)中说:“在建筑中必然出现的伟大变革,正如出现在思想、政治和手工业方面的变革一样,都不是天然力量的自发结果,而是由个别人物的意志所造成的。”这种说法或许会被认为有些夸张,但当它被用在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这样当量的人物身上时,分量还是对等的。某种程度上,正是培根以他所擅长的“知识的力量”预言并催化了英国自然式园林的出现,在《论花园》(Of Gardens)中,培根写道:“种植花园是人类乐趣中最为纯洁的事,也是人的精神的最好的滋补品。没有花园,建筑物和宫殿将成为粗俗的人工制品。正如人们看到的,在时代走向文明雅致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先创造建筑的辉煌,而后创造园林的幽雅,仿佛园艺学是更接近‘文明’的完美造物。”“全能的上帝率先培植了一个花园。的确,它是人类一切乐事中最纯洁的。它最能愉悦人的精神,没有它,宫殿和建筑物不过是粗陋的手工制品而已。”
与培根一同被称为“英国自然式园林先驱”的是弥尔顿(Jone Millton)。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的第四章中,弥尔顿描绘的上帝的园林“伊甸园”激发了17世纪英国民众对自然式园林的想象:“碧玉清泉如何流成涟漪的小河,/流着东方的珍珠和金砂,/在两岸垂荫之下蜿蜒曲折地,/流成了灵醴甘泉,访遍每一株草木,/滋养乐园中各种名花,/这些花和园艺的花床、珍奇的/人工花坛中所培养的不同,/是自然的慷慨赐予。”尽管不曾亲眼看到“光荣革命”,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清教徒家庭的弥尔顿毕竟也热血澎湃地写过《为英国人民辩护》(Defensio pro Populo Anglicano)。柯林斯指出:英国自然式园林是随着历史本身成了一门认识学科而出现的,这种突破同时出现于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的《美学》(Aesthetica)和温克尔曼(Johan Joachim Winckelmann)的《古代艺术史》(Geschichte der Kunst des Alterthums)里认识论的词句中。时至18世纪末歌德的年代,《亲和力》(Die Wahlverwandtschaften)中已经因为造园而引发一场形而上的情殇,而在孟德斯鸠的年代,初识英国花园的孟德斯鸠想必还正体味着弥尔顿笔下“同你谈话,我总是忘掉了时间以及季节的转换”式的清新。
在“任何专制国家的教育目的都是在极力降低国民的心智”这样的“硬话”之外,以现代人眼光来看,频繁出现的《论法的精神》中的以“climat”为基础的“普遍精神”理论也带有某种启蒙年代的“小清新”。《论法的精神》中明显体现出孟德斯鸠对“北方气候下的人”的偏爱:“炎热地区的人怯懦如同老人,寒冷地区的人骁勇如少年”;“北方气候下的人恶习少而美德多,非常真诚和坦率……温暖地区的人风尚不定,恶习无常,美德也无常”。这些观念在现代人看来很可能不以为然。倘若相信“法意”下暗含着“酒精”,甚至还有说法认为孟德斯鸠所称“在炎热的国家,由于血液中的水分流失严重,必须多饮水以补充流失的水分,但不宜饮酒,因为饮酒将使剩下的血球凝结;相反,在寒冷的国家,血液中的水分总是很充足的,饮酒不会导致血液凝固,反而能促进血液运动”实际是在为孟德斯鸠自己要向英国出售葡萄酒辩护,而他对英国政制描述的失真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的序言中请求读者“对一部20年的著作不要浏览片刻就得出结论”。除第一道大门门楣上的铭文外,孟德斯鸠在拉布列德城堡第二道大门的门楣上也镌刻了铭文:“Deliciae domini”(主之喜悦)。《论法的精神》这部包含了近3000脚注的巨著共分六大部分、31篇,最常被后人引用论证的主要是前两部分。然而,在很容易琅琅上口的“自由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之外,人们经常忽略孟德斯鸠故意回避了“自然法”。自阿奎那(Thomas Aquinas)编纂《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ca)以来,欧洲自然法传统带有鲜明的神学色彩,相信自然法就是上帝刻在人们心中的律法。在论述“神有神法、野兽有它们的法、人类有自己的法”时,孟德斯鸠说得颇有些暧昧,他并没有明确人的“法”是人作为道德主体主动为自己制定的,还只是和其他动物一样被动遵循上帝为其制定的自然法。法语中的“loi”指“实定法”,但同时也有“定律”、“规律”的意思。孟德斯鸠提出:人和其他动物不同的是,“作为智能动物,他会不断违反上帝确立的定律,并改变他自己建立的法律”。但另一方面,作为一种“感觉动物”,人受制于错误、无知以及“成千上万种激情”,让他经常忘记造物主、同胞甚至自己的真性,因而需要上帝的律法、道德的律法和政治与民事的律法加以不断约束和提醒。
在《论法的精神》的后四部分中,与其说是给“法的精神”下了一个明确的定义,不如说是以“气候”或“地理”的名义探寻了各国的律法“风土”。这英国自然式园林般的四大章节虽然占据了全书的主体,却经常被后人忽视或断章取义,或许只有亲身处在自己营造的拉布列德城堡的英式花园中的孟德斯鸠才真正明白其中的“意图”(dessein)。孟德斯鸠断言,植物不过是物质总运动的偶然结果,并坚持认为:植物世界的结构是机械的,人也是一台机器,和植物一样受物质因素的支配。这听起来很像是出生在波尔多的每一个继承了家族葡萄园的后代共同的宿命信仰。
拉布列德城堡中居住的最后一名孟德斯鸠家族成员是雅奎琳·德·夏芭内女伯爵(Countess Jacqueline de Chabannes),她是孟德斯鸠最年幼的女儿德尼斯(Denise)的后代。德·夏芭内女伯爵于2004年去世,由于没有子嗣,她安排这片产业在自己身后对公众开放。孟德斯鸠写作《论法的精神》时的房间以及图书室至今保留着17世纪时的原貌。面积216平方米、带有高挑拱顶的图书室内拥有上千册源自孟德斯鸠在世时的藏书。1994年,德·夏芭内女伯爵将图书室中的全部藏书与手稿授权托管给波尔多市立图书馆,这批珍贵遗产由此得以完整保留。
孟德斯鸠家族其他的产业早已四散,但其中诸如赫许城堡(Châteaude Rochemorin)、缤飞城堡(Châteaude La Bienfaisance)、巴克龙酒庄(Château Bacalan)、圣昂酒庄(Château Saint Ahon)等如今仍活跃在波尔多的葡萄酒世界。说“法意”是“酒精”可能只是个臆测,但“风土”对于葡萄酒确实已经成为经典概念,“法的精神”在它的学术世界中更是如此。孟德斯鸠笔下的“自然法”没有给人在出生时选择“风土”的权利,但写作《论法的精神》时孟德斯鸠自己选择了拉布列德城堡,拉布列德城堡也包容了孟德斯鸠的停留。尽管孟德斯鸠曾有名言“人在悲哀之中才真正像一个人”,在1755年写给古阿斯科的书信中,孟德斯鸠说:“空气、葡萄、加龙河畔的葡萄酒以及加斯科尼方言的笑话,这些都是治疗忧郁的良药。”